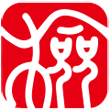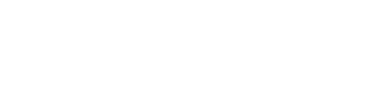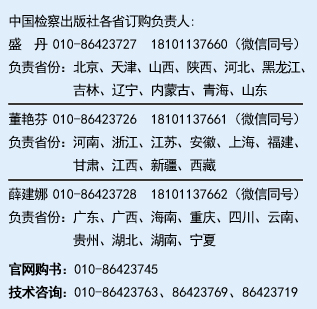二、非自愿供述和声明
公约第3条规定,禁止酷刑和非人道以及有辱人格的待遇。
在格夫根诉德国案中,警察以酷刑和其他的粗暴待遇威胁法兰克福一名法律系学生供述被绑架的警方认为仍可能幸存的男童的下落。该嫌疑人作出了导致自我归罪的供述并带领警方找到了其处理男童尸体的湖边。男童尸体的验尸报告和嫌疑人汽车轮胎留在抛尸现场的印记作为证据被用于法庭审判。该案中所有的非法供述均被禁止使用。①人权法院大法庭认为,警方的威胁构成“不人道和有辱人格” 的待遇,虽不构成“酷刑”,但构成对公约第3条的违反。由于被告人在法庭上作了有罪供述,国内法院判决被告人在法庭上作出的证言不再属于违反公约第3条的派生证据,且该案中被告人有律师帮助,国内法院仅依据被告人在法庭上的有罪供述对其作了有罪判决,仅将非法证据用作印证其供述真实性的证据。
人权法院大法庭认为,公约第3条所指称的有辱人格的待遇“囊括了一个民主社会中的最基本的权利” 并基于此而“不存在例外情形”,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比如在反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或者是与被指控的犯罪性质相关的犯罪中。
执法官员的行为是否构成“酷刑” 或者“非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取决于案件的整体情形,比如非法对待的时间长度、非法对待对嫌疑人的生理或者心理所造成的影响等,“嫌疑人的性别、年龄以及健康状况等”,“非法对待的动机与目的”和“现场情境,比如气氛的紧张度和情绪”。人权法院认为“非人道” 系“有预谋的,持续数个小时,造成被害人身体伤害或者强烈的生理和精神损害的行为”,“有辱人格”系使得被害人“感受到恐惧、痛苦和羞辱和贬低的自卑以及打破其生理和道德上的抵抗力”或者“导致被害人作出违反其自愿性的行为”。当非法行为被认定为“酷刑”时,这意味着官方的行为存在“故意造成严重的、残酷的伤害的非人道待遇”,同时,伴随着“目的性要素”,比如“为获得证据材料,对受害人进行惩罚和威胁”。对嫌疑人以违反公约第3条的任何一种行为相威胁, 比如酷刑, 均至少构成非人道待遇。对违反公约第3条的行为的证明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尽管这可能基于推论和不可反驳的事实推定。比如,当某人被警察拘留时是健康的,但是释放时受了伤,那么此时,政府负有合理说明该人受伤是如何造成的责任,如果政府未能履行这一义务,则意味着政府的行为将构成对公约第3条的违反。当公约第3条被违反时,人权法院需要作一项全面的审查,即国内法院对事实的审查判断并不能代替人权法院对事实的审查判断。
在格夫根案中,人权法院认为,警方对受害人的威胁造成了“巨大的恐惧、极度的痛苦以及精神损害”,但是未能发现“造成长期的心理问题”。人权法院认为警方威胁被害人的目的是在高度紧张和情绪化的情境下获取案件信息,动机是挽救被绑架儿童的生命。然而,人权法院进一步强调道:刑事侦查中无论受害者的行为或政府当局的动机如何,都禁止虐待嫌疑人。即使在个体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也不能施加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这项权利在威胁国家安全的公共紧急情况下也不允许减损。第3条以明确的方式加以界定并承认每个人都有绝对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遭受酷刑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即使是最困难的情况下,亦不受剥夺的权利。第3条规定的权利的绝对性的理论基础不允许任何例外或正当性因素或利益平衡,无论有关嫌疑人的行为和所涉罪行的性质如何。
在确定以酷刑相威胁是否构成酷刑或只是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时,人权法院大法庭认为:“对某种特定的生理酷刑威胁是否构成精神折磨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取决于全案情形,包括所施加的压力的严重性和造成的精神痛苦的强度。”通过适用这项检验标准,人权法院大法庭判决格夫根案中警方的威胁系非人道待遇,而非酷刑。
人权法院将公约第3条和公约第8条进行了对比,后者总是需要运用权衡理论作“全面审查”,以决定是否违反公约第6条下的公正审判权。人权法院指出, “在刑事诉讼中使用违反公约第3条取得的证据需要考虑特殊因素”,因为“使用此类证据”,由于该证据的取得违反公约规定的核心和绝对权利,这总是会引起关于诉讼程序的公平性的严重问题,即使此类证据的使用在定罪中不具有决定性作用。
由于格夫根案中,国内法院并未使用警方通过违反嫌疑人自愿性取得的供述,大法庭需要处理由非法取证进而派生的实物证据的证据资格问题,即在审判中使用的被害者尸体和格夫根的汽车的轮胎痕迹。就这一问题而言,大法庭认为:“如果警方的暴力行为被认定为酷刑,那么,以暴力取得的非自愿的实物证据至少不应当被用作证明嫌疑人有罪的证据,不论其证明价值如何。” 尽管其他结论可能间接地使公约第3条所禁止的有责性的行为合法化。
关于通过低于酷刑的非人道以及有辱人格的方式取得的实物证据是否导致审判的不公正,就此而言,不论证据的重要性、证明力和被告人对该证据的资格和使用是否享有质证的权利等, 人权法院未在判例法中对该问题予以明确。人权法院认为尽管格夫根案中的被害人的尸体和汽车轮胎痕迹系违反公约第3条进行取证的结果,公约成员国中对于毒树之果理论的适用也富有争议,包括“必然发现原则”,但人权法院大法庭仍进行了权利和利益的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