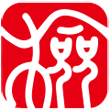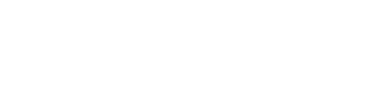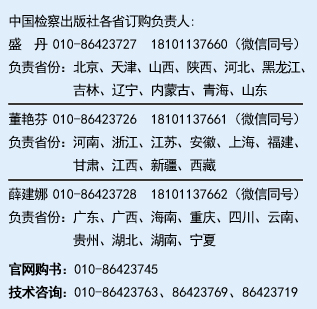在“第二层次的分析”中,使用证据是否符合第6条要求的“公正”,人权法院权衡了潜在的实质性的前审判规范以及通过违反该规范获得的证据的证明价值。当规范违反被认为是“严重的”,如故意威胁与折磨,比如德国的G案中(绑架小孩案),法院倾向于排除证据,考虑到遏制这种恶劣的取证行为的必要性,就像一个美国法庭发现一名官员并非出于善意的违反宪法。正如人权法院在G案中的表述,“使用违反第3条规定取得证据的可能鼓励执法人员使用这些不法取证方法,因此法律绝对禁止”。
在许多涉及违反公约第6(3)(d)条关于被告人对质权的案件中,人权法院对证据发现真相的性质进行了权衡。在这一领域,传闻证词(抛弃对质权)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其固有的不可靠性,因此,人权法院很快发现,在刑事案件中使用这些证据作为定罪的主要证据构成了对人权公约第6(1)条和6(3)(d)条的侵犯。一旦证据的证明价值成为影响因素纳入公正审判分析(第二层次分析),此时,判断方法开始看起来更像一个欧洲大陆国家浸泡在询审问制传统之中,即“所有证据在逻辑上相关的”,而不是一个普通法体系,即“主要关心证据是否可采”的问题。欧洲大陆的国家不太可能将证据排除在“寻找真相之外的理由”之外,例如以非法方式获得但是有可靠性的证据。特别是美国愿意为了实现其他价值而牺牲发现案件真相。
在实质性规则违反之外,人权法院通过“公正使用”模式弥补不公平,从而使非法获取的证据能够被使用,而不是通过排除证据来先发制人地保护公平,后者更多地反映了美国传统的做法。人权法院认可通过补偿机制弥补取证手段的非法性问题。此类补偿机制与导致证据不具有合法性的取证问题并无关联性。人权法院似乎是在“恢复”公正,如果证据具有很高的证明价值,那么证据就更容易被证明,实物证据也是如此。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法庭不愿意在违反公约第8条的隐私权的情况下,认定公正审判权被违反,这通常会导致发现的实物证据或者通过窃听来获取的言论被排除。
在涉及隐私权的案件中,人权法院始终坚持“必须慎重考虑证据的资格问题,包括证据的可靠性、准确性存疑的案件情形,也包括缺乏其他证据印证但公正性不存疑的案件。人权法院进一步指出如果证据确实、充分且不存在定案的风险,如是,对补强证据的需求也相应地减弱”。然而,不同性质的违法行为,比如违反公约第3条的禁止不人道的和有辱人格的措施,法院认定使用借此取得的具有高度证明力的证据(通过使用催吐剂提取的可卡因)也构成对公约第6条的违反。如果这种侵犯等同于酷刑,那么更严重。在格夫根诉德国案中,具有真实性的“间接证据”是通过虐待包括酷刑的威胁取得的,人权法院认为:通过威胁取证违反公约第3条,同时也对公正审判权构成侵犯。总之,人权法院似乎并没有考虑侵犯隐私权的权利,这是在公约第3条的基础上进行的酷刑或不人道或有侮辱性的待遇,在后一种情况下将排除证据,但侵犯隐私权的情况下很少排除证据。人权法院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违反审前的律师帮助权和沉默权而取得的证据的证明价值。
在Jalloh案中,人权法院强调了另一项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即“刑事调查中所涉及的公共利益”。但人权法院也进一步强调,“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并不能证明侵犯上诉人的辩护权的本质的非法措施的正当性”。在涉及违反公约第3条的案件中,人权法院表示,违法手段所获得的证据不能使用,“不论被指控的罪行是否严重”。
至于对公约第6条保护的免于自证其罪权和沉默权的侵犯,人权法院表示:“第6条公正审判权要求的免于自证其罪的权利适用于一切类型的案件。公众的利益不能成为侵犯该项权利的抗辩理由。”
在刑事诉讼的预审阶段,违反了律师咨询权也是如此。法院认为,保护原则阐述了“特别要求在严重的指控的情况下,因为可能面对最重的惩罚,民主社会需要最大可能的尊重公平审判的权利”。法院的这种转变可能引发混乱,如果公约第3条是绝对权利,就不需要任何权衡事实真相或者公共利益。
因此,人权法院视野中的违法取证行为可类型化为三类,此三类不同的违法行为对应着三种不同的非法证据评价模式:(1)侵犯隐私权违法取证。该类行为很容易被净化,从而使证据获得可采性;(2)违反其他公约权利的行为,这时需要更加严格的权衡;(3)如果使用证据将必然违反公正审判的行为。在对三类非法证据的可采性进行判断时,证明价值的作用在第一种侵权类型中对证据可采性有决定性作用,在第二种情况下需要进行权衡,但在第三种情况下不再考虑证明价值。
但是,是什么使得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严重到足以在人权公约和国家宪法中受到保护的程度),比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比如侵犯了免于自证其罪权,违反公约第3条,或违反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要轻微呢?可能的解释是,人权法院并未贬低侵犯隐私权的严重性,而是认为侵犯隐私权对审判公正的冲击相对较弱。因此,即使最严重的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在刑事诉讼的意义上,也不被认为具有相当的违法性,因此,使用由此取得的证据也不被认为存在多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