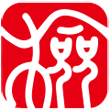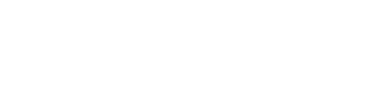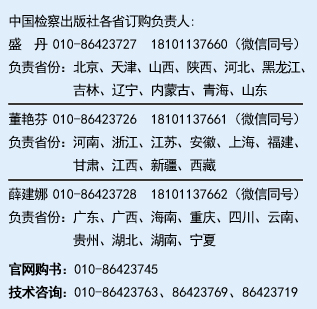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地方、部门和社会公众建议明确“从宽处理”的具体含义;有的建议修改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的建议修改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明确为“在诉讼程序上”依法从宽处理。
有的常委委员提出,要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对轻罪认罪认罚,逃避重罪处罚的情形。有的部门、地方和社会公众提出,认罪认罚案件处理应符合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不能放宽证明标准;有的提出,对于在不同诉讼阶段认罪认罚的,应当给予不同的从宽幅度。
有的地方、社会公众建议对适用的案件范围作出限制。有的建议限定为基层人民法院审判的可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或者可能判处三年以下刑罚的轻罪案件;不适用于未成年人案件;对故意杀人、强奸等严重罪行,没有刑法规定的从轻或者减轻条件,认罪认罚也不应从宽;对司法机关已经查实的犯罪,认罪认罚也不应再从宽处理。
有的建议明确对认罪认罚案件应当采用相对简化的诉讼程序。
2. 草案二次审议稿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有的部门建议进一步明确认罪认罚的含义。有的社会公众提出,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罪行就应当从宽处理。有的社会公众建议删去“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只适用于被告人。有的建议对故意杀人、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毒品犯罪、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等严重犯罪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有的常委委员提出,从宽处理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实体权利,应在刑法中规定。有的社会公众建议明确“从宽处理”的含义,是否包括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建议改为“从轻、减轻或免除”;改为“从轻处罚”;建议对不同诉讼阶段认罪认罚的给予不同的从宽幅度,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尽早认罪认罚。
【条文精解】本条是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规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首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既是实体法上的制度,也是诉讼法上的制度。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实体法上通过在量刑、刑罚执行等方面规定一系列从宽措施,促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被判刑人自愿认罪认罚,有利于其悔罪和改造,消除社会矛盾。刑法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判处刑罚。在此基础上,对于有认罪认罚表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法也规定了一系列从宽处理的制度。比如,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根据刑法规定,对于认罪认罚的犯罪分子,结合考虑其悔罪表现、是否有再犯罪的危险等方面的因素进行考量,还可以适用缓刑、减刑或者假释等制度。这些都是认罪认罚从宽在实体法上的体现。刑法一直坚持和贯彻这些原则精神,历次修改刑法,很多内容都体现了这些要求。比如,2011 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一方面根据新形势下惩治犯罪,保障社会秩序的需要,作了一系列趋严的修正,如增加7 个新罪,扩大10个罪的构成要件范围,提高、增重8个罪的法定刑,扩大特种累犯的范围,提高无期徒刑犯减刑、假释需要实际执行的年限等。另一方面也作了不少趋宽的修正,如取消13个罪的死刑,对已满75周岁的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对未成年人犯罪、怀孕的妇女进一步从宽处理,对假释需要实际执行的年限作出例外规定,对于犯罪分子不具有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等。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修正案(八)的基础上,又取消9个罪的死刑,并进一步提高对死缓罪犯执行死刑的门槛等。
认罪认罚另一方面体现在程序上,即在能够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情况下,尽量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更为轻缓的强制措施和程序处理措施,适用更为便利的诉讼程序,使刑事诉讼过程尽量对包括被告人在内的当事人的各种权利造成较小的影响,使案件能够尽快得到处理,避免当事人及其他人的合法权利长期处于未定状态。比如,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采取取保候审措施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可以取保候审;对于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怀孕或者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等特殊情况的,可以监视居住。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法律规定的一些特定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告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可以从宽处理等。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就是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在总则中明确出来,为具体程序规定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各项程序措施提供基本依据。同时,对认罪认罚案件,在强制措施、量刑建议、审判程序、办案期限等方面,作了一系列完善性的规定。